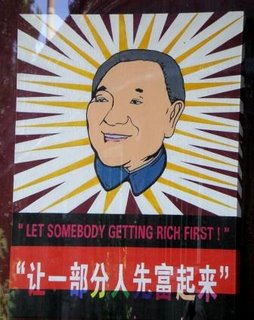《联合早报》 2006年11月27日也许是因为美国咖啡连锁店Starbucks的无远弗届,人们如今把咖啡看成是一种全球化的象征,甚至将中国茶和咖啡作为两极对立的意象――传统vs现代,中国vs西方,在地化vs全球化。龙应台在2003年中卸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后,再次刮起龙卷风的《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一文,就以最后一组意象掀起了文化危机感的反思。
尽管如此,我不得不说,在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国家短短的历史里,喝咖啡是我家族的悠远传统,而且可以分别追溯到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源头。
小时候,我到祖母在大坡吉灵街的住家,狭窄而陡峭的楼梯通往店屋的二楼,马上就是一个小小的起居间,有一张圆形的云石饭桌,上头总是摆着一个瓷壶和几个杯子,壶里永远是随时倒得出来招待客人的黑咖啡。我父亲大概从小就把咖啡当开水喝长大的,夜里再晚喝了咖啡,他都能够睡得着。
外公家里的生活方式则完全不同。住在外公位于Devonshire Road的家里的那几年,每天早上,他总是要母亲给他准备西式的早餐:两个荷包蛋,两片牛油面包,再加上一杯咖啡。什么咖啡?即冲即溶的Nescafe!那可是70年代初的事哦。据说,外公在60年代初在苏菲亚山的三山学校当校长的时候,就已经是吃这种早餐了。
能够说我家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很“全球化”了吗?那种喝咖啡的传统,在我的直接认识中,可发生在全球冷战最激烈的年代;况且,父亲和母亲两家的传统,显然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渊源。是否可以再往前追溯?譬如说以咖啡当水喝可能是南洋华人数十年累积的生活习惯,而外公在家乡福州时可能也受到五口通商近一个世纪的西化影响。老实说,我也不是太确定。
不过,我喝咖啡的个人历史,倒也和这两个家族传统没有太大的关系。
到台北念大学之前,我不记得自己有每天喝咖啡的习惯。校门隔着罗斯福路对面的商店三楼隐藏着一间风格独特的咖啡馆,叫做“蓝调”,常常播放着George Winston的那张钢琴曲 “December”,召唤着我每个星期那三个没有上课的下午总要准时往那里报到。“蓝调”最贵的咖啡是台币90元的蓝山,我不算是有钱的学生,每个月领的一点公费,比起很多本地生和侨生要宽裕一些,也够我喝一杯最便宜的50元的巴西咖啡,泡一整个下午。我大学时期写的好些散文,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蓝调”的咖啡是用蒸馏的方式煮的,喝起来味道淡淡的,摆在桌上却满室生香。我一直记着这个味道,往后总尝试找回,潜意识或有意识的,想要找回少年的记忆。可能因此,在新加坡我最喜欢的咖啡是在Coffee Club而不是Starbucks,是前者的蒸馏的巴西咖啡,而不是后者的喝起来像龙沟水的过滤咖啡。
说到台北的咖啡馆,那简直是隔条巷子就有一间;在大学附近,更是一条街上就有三间五间,而且几乎都不是国际连锁店,每一间都风格独特,招待个人化。前几年曾经看过市面上有两三本专门介绍台北咖啡馆的书,而常想把台北咖啡馆作为学术研究课题的S更是可以随时为将要到台北的访客画一张咖啡馆索引图。
我曾经在天母的一间咖啡馆,坐了五天喝了十杯咖啡(因为可以续杯,也就是refill),完成了剧本《市中隐者》。店名叫什么我已经忘了,不过记得店外有一张招贴写着“一回生两回熟”。咖啡馆里是欧洲贵族式的装潢,不过相当陈旧,照明也非常不足,主要的光源是每张桌子上一盏小小的印上深色图案的纱布灯罩的台灯。我就将台灯拉近我的稿纸(是的,那时还是用笔在稿纸上书写的),伴着半杯已经凉掉许久而又舍不得喝完的咖啡,昏昏暗暗的连写了五天。
后来常去的是在师大路巷子里的Café Oso,门外有一只比人还高的北极熊站立着迎接客人。这家的咖啡烹煮还真讲究,不同种类的咖啡,根据原产地的习惯,得用不同的器材和方式,譬如说,哥伦比亚咖啡是用蒸馏法,苏门达腊曼特灵咖啡则用泡煮法。连续好几年,都是在十二月假期的时候到台北,总要在这里度过一两个下午,和咖啡馆里的小妹也会聊上几句。最近一次重返Café Oso是在一月,小妹一见到我,就说:“怎么这回晚了一个月?”我吓了一跳,每年才来两天的客人,竟然记得那么精准!
台北最有人文气息的咖啡馆,要算是“明星咖啡馆”了。擅于将上海的富贵气派与台北的平民性格进行对比的小说家白先勇,曾经出版过以此为名的散文集。“明星”的老板原是在上海开西饼店的白俄罗斯人, 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军民一起来到台北。白先勇的小说里创造了上海与台北两地对比的意象,还借用刘禹锡的诗,说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过,“明星”来到台北之后,倒是成了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艺术的发源地呢。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诗人周梦蝶曾经在“明星”楼下的骑楼摆摊子卖诗集的都市传奇。今年初再访“明星”,入口处的那张舞蹈家林怀民二十岁时摆pose的黑白照片,引发无限对于台北人文景观的遐想和回味,我的那杯咖啡是什么味道竟也忘了。
我不能没有咖啡的生活,大概就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吧。这种其貌不扬的饮料,要如何铺展一个长逾千年的洲际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再把我的个人历史缀织上去,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呢。古早的传说中,在公元九世纪,一个非洲衣索匹亚的牧童见到他的山羊吃了一种红色的果实后特别活跃,他一试之下也觉得精神亢奋,人们就开始以咀嚼这种果实来提神。发现果实的地点,是衣索匹亚一个历史上叫做Kaffa的地方。果实的栽种培植,在阿拉伯地区开始推广,后来再由欧洲的旅行家带到西方。因此,从字源的角度来说,先有阿拉伯的qahwa,传到土耳其而产生kahve,到意大利成了caffè,再到英格兰就是人们现在熟知的coffee了。
也许因为咖啡最早传到欧洲是在威尼斯港上岸――那已经是十七世纪初的事了――意大利式的浓缩咖啡espresso是所有欧式咖啡的基础,恐怕也是咖啡文化的根本所在。现在人们爱喝的各种各样的“花式”咖啡,像cappuccino, latte, mocha等等,都必须以espresso为底。最近我到斯洛文尼亚的首都Ljubljana开会,这个城市很靠近威尼斯,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吃过晚饭后叫咖啡的话,如果不事先说明,侍者就自动端来一杯espresso,连牛奶都没有,更别说是其他的花样。在巴黎则还有二选一的机会:我在香舍丽榭的bistro点咖啡,侍者会问: “Café noir? Café au lait?” 初次听到café au lait,脑筋没有转过来,觉得奇怪为什么法国人学起英国人唱起足球场上的胜利之歌: “Olé, olé, olé, olé…”
我喝的当然是café noir,也许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味道吧。加糖不加糖,对我来说并不是太重要——如果加的话,那也是少许,大概半个咖啡匙(放在咖啡杯里的不要叫“茶匙”ok?它会有认同危机的)。加了牛奶的话,我会产生意识错乱:究竟是加奶的咖啡,还是咖啡味的牛奶?的确是叫人感到困惑啊――加了牛奶不是就辜负了咖啡的香醇?不过,我总觉得espresso太浓了,而且太小杯,头一仰,一口就喝完。像我在台北泡咖啡馆写散文和剧本的情况,整个下午要仰头喝掉多少杯的espresso啊?如果我是衣索匹亚的那只山羊,可能会变成天鹅飞上天空了。所以尽管我实在不喜欢美国式的咖啡,我点的却很反讽的往往是一种叫做Americano的咖啡。不过,那不是美国人常喝的过滤式咖啡,而是同等分量的espresso和热水掺合的合成品。这种hybrid咖啡,看来也蛮适合我这种崇拜多元文化的性格呢。
泡咖啡馆显然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喝那杯咖啡,而是一种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生活方式了。的确,喝咖啡是一个过程,激发创造力是其产品――以咖啡来说,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如今被看成是对健康有害的三样东西:烟、酒、咖啡,如果没有它们作为催化剂,历史上哪里产生得出那么多杰出的文学艺术?烟酒暂且不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史,恐怕不小的部分是一部咖啡史呢。以今天的城市来说,台北哪一间诚品书店里没有一个卖咖啡的角落?北京的万圣书园里不也有一个醒客咖啡馆吗?
我从台北念完书回来,总想找一个可以感受一点人文气氛的咖啡馆。80年代末的新加坡有许多日本百货公司,而比较有感觉的咖啡馆都是在里头。我最常去的是Liang Court的Daimaru以及Raffles City的Sogo,尤其是后者,咖啡馆里向北有一整面落地玻璃墙,往外看就是古老的圣安德烈教堂,斜角则是首都戏院。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就非常“哈欧”,喝咖啡应该就是从欧洲学来的。美国也学欧洲人喝咖啡,不过“文化”一到美国就变成“次文化”。日本人不同,他们学会喝咖啡之后,无论饮具或烹煮方法,显得更为讲究和精致。可惜的是,就算每次到Sogo喝咖啡他们都给我一套不同的设计雅致的fine bone china杯子,咖啡香以外总还少了一点什么。
要找那种咖啡香和书香揉和的味道,在新加坡可是一个蛮不小的挑战。这里的咖啡馆几乎都是没有多少个性的连锁店,更不用说书店可能比宠物店还少。后来还是咖啡馆专家S的介绍,我才知道在Mohammad Sultan Road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Book Café。顾名思义,馆里有几个摆满各种书籍的架子,还有两台电脑,让客人免费上网,不过听说速度超慢。最有意思的是,如果坐在户外,正好就可以看到斜对面那座著名的半空中有个玻璃缸泳池的建筑。每个月的某个晚上,这里有一个固定的诗人聚会,朗读近作或交流诗观,颇有文学沙龙的气氛。
最近发现的另外一个惊喜,是隐藏在Hillview住宅区里头的Gone Fishing,是J的好介绍。据说老板是做生意做得腻烦了(今年他还得了企业精神奖呢),想要找一点“有意思”的事来做。店外看起来并不起眼,相当杂乱和随意。进到店里,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几面白墙都填满了各种放浪不羁的画作,显然是某些才华横溢的画家留下的痕迹。走近一看,画家的杰作之上或者周边,看来是客人随兴的涂鸦文字,有的读来像诗,有的是生活感触,有的是对这家咖啡馆的赞美之词。店里某个角落,也有一个摆满了的书架;每个月的某个晚上,也有聚会,在这里是哲学家的论坛,听说是由一个哲学系研究生主持的。
说我小资情调吧,说我西化吧,咖啡在我的血液里流动已经是半辈子的事,而且会继续流动下去,并刺激着我的思考和写作。追溯起根源来,这个部分的个人咖啡史,很可能是从母系家族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看,父系家族又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影响呢?
比起沙龙式的咖啡馆,我去组屋邻里的羔呸店的次数恐怕远远超过,而且所到之处遍布新加坡各个角落。80年代开始,各个食物摊位实行起“自助服务”之后,羔呸店里就只剩下饮料是有uncle或auntie到桌前服务。坐在羔呸店里,也因此不断可以听到uncle或auntie的响亮而拉长尾音的声音,此起彼落:kopi, teh-o-siu-tai, kopi-see, teh-bing等等,一种单调中有变化,却让人觉得熟悉而亲切的节奏。我听过最长的一种饮料是:kopi-o-kao-ka-tai-bua-sioh,一共有八个音节呢。这究竟是什么饮料?正是:咖啡,不加奶,少加热水调稀,双份糖,不要太烫!说到个人化与专业化的服务,嘿嘿,谁又能够比得上羔呸店这套具有系统的既复杂又精简的语汇?最惊人的周到服务,是有一阵子我常到某个羔呸店吃早餐,每天当我停好车子,走到习惯的位子要坐下来的时候,uncle就已经端了一杯kopi-o-siu-tai走向我的桌子!
具有民间性格的羔呸店里,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文色彩的。傍晚到羔呸店,往往坐了不少人,手里都拿着一份《新明》或《晚报》,从封面读到封底。也许uncle们关心的主要是抢劫谋杀等社会新闻或明星怀孕等娱乐小道,报纸某页的一则新书介绍或者戏剧漫谈,很可能也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偶尔下班后喜欢到羔呸店,也买一份《新明》或《晚报》来看;或者,像这几天,在一杯kopi-o-siu-tai的伴随之下,翻阅着N从伦敦寄来给我的新书《New Poems on the Underground 2006》。
郭宝崑在80年代写的剧本《羔呸店》,叙述一个坚守老店的祖父和想要把传统羔呸店现代化的孙子之间的重重矛盾,流露出沉重的失落感。陈子谦几年前的短片《福协隆》,记载55年历史的老羔呸店,在城市发展的前提下被迫关闭的命运,也散发着浓郁的怀旧情感。我如今常去的羔呸店,虽然在血统上是郭宝崑和陈子谦所描述的南洋羔呸店的延续,不过,就如陈子谦在短片中带着忧郁声调的旁白所说:“如果要把这一切拍成电影,能拍到的都只是点缀;真正流露在这里的人情味,又要如何捕捉?”
是啊,我平凡的文字,又怎么能够记录得了那么错综繁复、源远流长的咖啡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