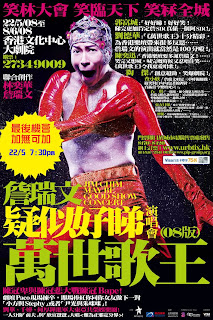標準與多元:新加坡劇場的語言展演
文︰柯思仁
 |
| 鍾達成編導演的《根》。圖片來源:Tuckys Photography. |
今年三月初,在香港上環文娛中心看了一齣新加坡戲劇《根》,由新加坡劇團「十指幫」演出,鍾達成兼任編導演。《根》是自傳性的作品,講述一個第三代的新加坡華人,到中國台山尋根的故事。尋根,在二十世紀移民史與殖民史的脈絡中,是文學與藝術敘事的經常性主題。新加坡人的經歷,在某個程度上,可能讓香港人產生共鳴。
《根》的特殊之處,在於這個單人劇演出中,身處不同的社會情境,面對不同的戲劇人物,演員鍾達成在華語、英語、粵語之間自由順暢轉換使用,交織成繁複多元的紋理,而又那麼具有說服力。現場滿座的香港觀眾,這些年來浸濡在三語兩文的環境,跟我這個來自新加坡的人一樣,享受著多語再現的多元文化的社會史與家族史,儘管某一些細節可能觸動不同的歷史參照與文化體驗。
作為一個新加坡成長的華人,劇中主人翁的社會性語言是英語,以英語展演他的新加坡身份,也由此產生他與華人身份的某種距離感,並界定他與其他地區華人差異的認同方式。當他與家人對話或表現內省式的內心獨白時,多以華語(國語、普通話)進行,展示這個語言指涉的家族聯繫及其在個人身上留存的深層文化印記。主人翁的尋根之旅,則以粵語開啟具有戲劇性甚至傳奇性的探索歷程,一方面展現潛藏記憶在逐漸開掘過程中的震動感,另一方面,也流露主人翁某種在接近想像的身份源頭卻又加深陌生感的荒謬效果。
鍾達成的華、英、粵三語皆流利生動,顯然上述的三語和三種戲劇情境的關係,不是順時性的,並沒有展示幾種語言之間此消彼長的態勢。劇場以外的歷史與現實情境倒並非如此。社會語言學家的研究顯示,新加坡華人的地方語言(主要是閩南語、潮語、粵語、客家話、海南話等)的使用率,從二十世紀1980年代以來已經急劇減少,華語的普及化在學校教育與社會運動的推行下快速提高,不過,在建國以來以經濟與政治為背景的國族建構工程中,英語已經取代所有語言成為最通行的共同語。儘管如此,在長時間脈絡中,當前社會的語言操練仍然展現多元並存、互相交集的現象。
像新加坡或香港這樣的多語社會,尤其是公共空間裡,不同背景的人交集互動,不時靈活自然地在各種語言之間交替轉換。這是一種社會現實,呈現繽紛多彩的景觀。新加坡兩百年來的近代史上,一直都是多種族形成的多元社會,包含馬來族、華族、印度族、歐籍人士、各籍通婚產生的難以界定種族文化屬性的多母語的後代,以及不同時期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等等。因應不同時代的社會動態與結構,馬來語和閩南語曾經是新加坡各個語言群體之間較為通行的共同語,而近二、三十年來則毫無疑問的是英語取得此位置。
對比於多語的社會形態,劇場表演中使用單一標準的語言,卻是歷史上的常態。1980年代中以前,生活中幾乎無人使用的「標準華語」,是劇場演員必須學習的語言。這種劇場語言,就像是當年廣播或電視節目中的華語,象徵一種純粹的、想像的、群眾必須齊力追求以完成統一國族身份建構的標準。經過數十年的詢喚與操演,結集各方力量,包括劇場、電影、電視、電台,以及學校裡的教學等等,「標準華語」也已經成為人們潛意識中展演身份的媒介。新加坡的英語劇場,也經歷類似的歷史過程,創造了以英國廣播公司為模範的「標準英語」。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從演出者的角度來說,劇場實踐往往必須預設特定的操用某種語言的觀眾對象,一方面,不得不服膺於社會想像中或操演中的主流語言所形成的壓力,另一方面,也配合社會上進行的國族身份建構工程而作出貢獻。尤其是大眾訴求的主流劇場,借用單一標準的語言進行表述,創造讓觀眾一致思考與感受的共同空間,也同時泯滅這些來自社會各階層觀眾在現實中的差異性。
從1980年代初開始,相對於大眾媒介的電視與電影,作為小眾媒介的劇場,開始形成一股從民間個人崛起的力量,提出另類於主流意識中通過標準語言展演的身份認同。至今仍然讓人記憶深刻的,是同在1985年首演的兩齣戲:郭寶崑的《棺材太大洞太小》、官星波的《翡翠山的艾美麗》。《棺材太大洞太小》有英語和華語兩個版本,由雙語兼通的郭寶崑編導,劇中演員分別用觀眾熟悉的生活語言,而非標準腔調的語言來演出。《翡翠山的艾美麗》則以新加坡式英語演出,不僅突破單一標準語言的規範,也將生活中逐漸形成的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是一種雜交式的語言,以英語為基礎,融合華語、馬來語、華人地方語言的詞彙與語法——帶進劇場空間。這兩齣戲的出現,被學者視為「新加坡戲劇」時代來臨的先聲。
三十年來,以(不同程度混雜的)新加坡式英語演出的劇場作品越來越普遍,數量也越來越多,幾乎形成新加坡人(表演者與觀眾)普遍認同的由民間創造的主流共同語,也可以說是流傳於民間的用以展演身份認同的符號,以及抗衡標準的外來語言(英國廣播公司腔調的英語)的媒介。不過,當新加坡式英語成為眾人追求與期待的另一種「標準」語言,它也顯然開始扮演過去的那些標準語言的角色,有意或無意的對於社會中的其他非主流語言形成邊緣化的態勢。
 |
郭寶崑編導的《尋找小貓的媽媽》,演出後創作團隊與觀眾交流。
圖片來源:實踐劇場。 |
多語劇場演出,在大多數時候,是不可想像的。即使像新加坡歷史上這樣一個多語並行的社會,幾乎沒有人能夠宣稱聽懂這個社會空間裡的所有語言。當觀眾在多語劇場中無法聽懂所有的表演語言,無法了解某些情境,不免產生被演出者排擠的疏離感。新加坡的第一個多語劇場,是郭寶崑編導的《尋找小貓的媽媽》,在1988年演出,其多語形式對觀眾形成的壓迫性感受,正是演出後議論的焦點之一。劇中的表演者使用幾乎新加坡各群體的語言,包括華語、英語、馬來語、淡米爾語,以及多種華人地方語言。不過,此劇的多語並非純粹的形式,而是其重要的主題。劇中主角是一個只懂得閩南語的媽媽,在華語和英語逐漸普遍的時代,喪失了她原有的生活機能與社會空間。國族想像與建構的過程中,主流強勢語言逐漸形成,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社會經濟脈絡中,看來像是不可避免的。與此同時,這種統一的語言,也往往具有排他性,對於屬於社會與權力邊緣的群體,像媽媽這樣無法使用主流語言的人,形成不可避免的壓迫與傷害。
《尋找小貓的媽媽》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產生,對於那個時代的演出者與觀眾皆造成巨大的衝擊。觀眾無法聽懂所有的語言,被強迫進入媽媽被邊緣化的處境,深刻感受媽媽的現實與心理遭遇。此劇不僅是將社會的多語情景再現於劇場空間,挑戰一般觀眾對於操用單一標準語言戲劇的認知,它也是對於社會現狀的質疑,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抗。郭寶崑後來繼續創作不少多語劇場作品,如《〇〇〇么》(1991年)、《黃昏上山》(1992年)、《芽籠人上網》(1997年)、《夕陽無限》(1999年)等等。在郭寶崑之後,也有好些劇團與創作者,進行多語劇場的創作,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不斷展演新加坡社會多元性的風貌。
近年的多語劇場演出,由於劇場技術的協助,使得字幕的使用更為簡易與普及,對觀眾造成方便,而不會像當年《尋找小貓的媽媽》的觀眾那樣被迫無法理解與參與。鍾達成的《根》,是這個時代的多語劇場,演出時即時投射中、英文字幕。(有意思的是,兩文字幕,加上演員的華、英、粵三語,來自新加坡的《根》倒也戲劇性的呼應了香港的三語兩文政策)。即使《根》沒有前一代人的多語劇場那樣的政治批判性,它的多語演出仍然展演新加坡社會多元性的精彩與可貴,並也提醒著我們,單一標準的語言,或者這種語言所承載的單一標準的意識形態,對社會中的邊緣個體可能形成的壓迫,以及對社會多元性的豐富景觀可能造成的戕害。
發表於: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藝評筆陣】
http://www.iatc.com.hk/?a=doc&id=43559